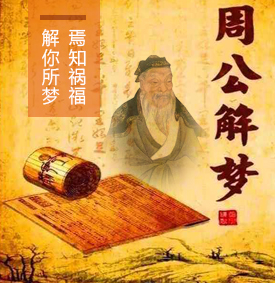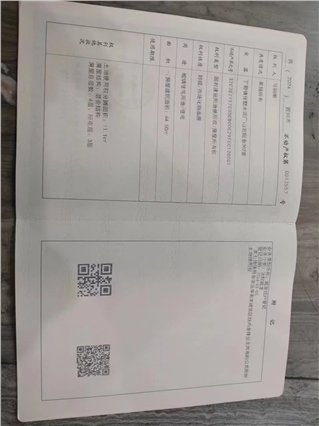春天里的思念——写给妈妈的歌
春天里的思念
——写给妈妈的歌
马金国
妈在江南小城宜兴郊区的丁山镇任墅水泥厂,买下了一处房子,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年。前年出差,路过丁山,专程去看了看妈的房子,那地方离镇里还有一段路,我下了长途客车,要了部三轮摩托,凄风苦雨,小车行进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,摇摇晃晃,天黑才见到了妈住的那栋楼,孤零零的一栋楼,有人的家里,早已上了灯,而妈的灯是再也不会亮了。前次来探母时,先是电话告知哪天到,妈早已翘首以盼,到得镇上时,定是还要打个电话的,告知她儿已到得家门口了,她会很仔细嘱咐:五里多地呢,坐小三轮进来,别太节省了,给三元就行了,看你是外地人会要你五元的。车到了,付了五元,转身要走,车夫:“你是来看上海人的吧”?(水泥厂的人都这么叫妈)“是的,那是我娘……”我便一下子止不住早已盈眶的泪水点点头,车夫是水泥厂的下岗工人,找了我两元钱。
妈平生节俭却待人厚道,在水泥厂住了两年,人缘是极好的,她患有严重的肺心病,高原来不了,在江南舅舅们家里治病,一治就是十年,后来在这儿买了房子,身边又无子女,给她请保姆,说啥她都不答应,独自一人住在三楼!每天要下楼,走一里多路去打开水,有时还要到五里之外的镇上去办事,这一切对常人来说都是举手之劳,毫不费力就能办的事,对妈来讲要付出几倍于常人的力气!她提着装有两个五磅暖瓶的包,打水走600米的路要歇5、6次,邻居们见了都会接过暖瓶包去,妈总是歉意地向邻里们道谢。邻居中有个叫小康的四川姑娘,也是这江南小镇中的“外来户”和妈特别投缘,对妈也特别照顾,每每下班,总是主动带两瓶水回来,妈戏称她为“丈夫”,可怜的妈妈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极是寂寞的,盼望着小康下班,成了一天中最大的快乐,热情快乐的小康总会给她带来许多消息:你儿子又来信了,你姑娘寄照片和钱来了。妈总会把信分别装订好,有许多句子还被勾红,旁边加了批注“这句话有道理”、“这个字不认识”。
我收存着妈妈遗留下来两个装订好的厚本子,一个是我们三兄妹写给她的信,我粗略地统计过,约有扬扬20万言,那是她居住江南12年的所有精神财富!另一本是她一笔一划非常工整地抄录的日本电视连续剧《阿信》的整个故事65页,也有3万字左右,她特别喜欢阿信,说她自己现在就是老阿信。有事没事她总会拿了出来一遍遍地读,以打发漫长凄苦又充满病痛的风烛残年!妈妈没有多少文化,读过几天私塾,解放后上过学堂,念过三年级,但是她是极爱读书、学习的,遇到文化高的人,就请人家把常用字和词组写下来,一遍遍地读、写,再经常用到写信当中去。从我记事起她就经常给三个舅舅们写信,我上了学,就开始当了妈的“小先生”,我读到初中,她就经常会有字和词组要问:国啊,这个妯娌和连襟是什么关系啊?十三、四岁的孩子哪能搞清那么复杂的关系?可为了不辱没“读书人”的脸面,我告诉妈妈:妯娌是姐妹,连襟是兄弟。对似是而非的答案妈妈有点将信将疑,但还是非常给面子:“哦,是这样。”工作以后经常给妈妈写信,她保证是每信必复,不过她的信只有我们兄妹才能完全读懂,诸如:麦(袜)子要勤洗常调(换),寸三领头(衬衫领子)要打(洗)清爽。这种方言加别字的语句只能在家庭成员中交流,不过也从来没有造成过理解上的障碍,因为那些文字里满含着妈妈的爱!孩子们怎么会读不懂呢。如今兄妹们聚在一起谈论起妈妈的信来,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,其中也会有许多妈妈搞出的文字笑话,反倒让我们觉得率真可亲的妈妈更加可敬可爱。
她虽然文化不高,但家教非常严格,对我们三兄妹的教育抓得特别紧,因为做人做事,我们都没有少挨妈的训斥和打骂。她有句口头禅:不识字,不要紧,不识事,苦终身。这句口头禅中包涵着“做事先做人”的简单道理。农场生活困难,我们家人口又多,家境自然贫寒,妈妈大我十九岁,我六岁就开始带弟弟、妹妹,八、九岁就跟着妈妈一起做事,拣牛粪、打柴禾、套兔子、割麦子、拾麦穗、溜洋芋,跟着妈妈到职工大院里缝被子、洗衣服、纺毛线,什么都干,别人都以为年轻漂亮的妈妈是我姐姐呢,我们收的活特别多,一个月下来能有20多元的收入,当时爸爸的工资也不过拿37元。现在回想起来,正是有了这样的历练和妈妈一贯的严格管教,才使我们养成了吃苦耐劳、勤劳俭朴、做事认真、责任心强、待人诚恳等许多品质。而当今的“月光族(月月花光,也叫月光王子、月光公主)”、“80后新人类”身上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品质,这种品质并不能直接从教育(含高等教育)中获得,它主要来自于大量劳动的历练和苦难的磨砺之中。
妈非常能干,能吃苦、有远见、有智慧。我说两件事:69年在新哲农场,妈那会30岁,我11岁上四年级,当时我家在一大队,大队上只有三年级,我要到场部去上学,离场部30多里地,没车去场部,母子俩只好背着行李,带上干粮,走上五、六个小时到场部去。才走出大队部,天就下起了雨,我们冒雨走着,过李洪义沟(沟里的第一户居民叫李洪义,75年我初中毕业去工作的时候,这里有了地名叫曲朗大队)的时候得趟水,正赶上山洪下来,我脚底一滑,就躺倒在水里了,妈把行李扔下,赶紧来救我,结果两人衣服裤子全湿了,干粮冲走了,还冲走了妈的一只鞋,没有办法,只好把我和妈的四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,背着打湿的行李走了半天才到直属队,碰上了藏民公社的一辆小驴车要去场部,妈给人说了半天,总算答应了,上了驴车我才看见妈的脚底,被殷红的鲜血和泥糊了一层,赶车人从他屁股下面抽出一块羊皮扔给了妈,让她裹着。87年上电大的时候,曾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写成了题为《上学路上》的散文,刊登在了《新生报》上,报社的阎老师还给配了些钢笔画,图文并茂,拿给妈看,妈说后来想起来都害怕,全丈着年轻,要不然我们母子早没命了。在妈装订我们三兄妹信件的厚本子里,我看到了《上学路上》。要不是妈有远见硬坚持着让我上学,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,我的许多小伙伴,现在有些境遇不好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辍学过早!
第二件事:妈是上海人,口音中一直带着温柔绵软的吴音,她62年从上海追随父亲来到青海,一呆就是30多年,但乡音不改!对上海始终保持着美好的向往,她认为上海就代表着文明、美好、进步,她向人介绍“阿拉上海宁(人)”时,充满着自豪感。在祁连的八宝农场,开荒、种地、积肥、烧灰,住地窝、睡窑洞,后来到共和县的新哲农场,脱土坯、挖药材、烧砖窑,农场劳力紧张的时候,组建了家属队,妈后来还当了家属队长。无论生活多么艰苦,环境多么恶劣,劳动多么紧张,她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生活习惯,收工回家她会经常带些花回来,家里的花瓶里常常插着些马兰花、馒头花什么的,她那双手就象花仙子的魔棒,几乎家徒四壁的窑洞、地窝子,经她一装点,就成了童话世界的仙境了。她讲卫生,爱美、爱整洁,她的床是谁也不能碰的,那是一张从上海托运来的旧宁式床(81年做了我的婚床),我们三个只有象消毒似的洗干净了,才有资格上床。我们在家里是一定要坚持讲上海话的,这对一个生在青海长在青海的孩子来说,并不是件容易事,妈妈做到了,在她的严格训练下,我们三个的上海话说得非常地道。94年我带着二十几个司机,从东北到珠海去,途经上海,师傅们风尘仆仆,满脸的高原风光,加上我又穿着一身警服,在登记住房时,几个女服务员在用上海话议论:这个警察一个人带了这么多犯人,你们要当心哦!我用上海话告诉她们,这都是我们的工人师傅,不要乱讲!她们非常吃惊,这个大西北的警察怎么也会讲上海话的?后来到姨妈家和表兄妹们用上海话交流,他们也非常奇怪,你们的上海话怎么会讲得这么标准的?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妈妈的良苦用心和智慧。
妈独居的两年里,我们三个都分别回去看过她,陪她生活上一段时间,那样的日子是我们母子的节日,病中的妈妈,脸上总是笑着,我去打水,她便会站在窗前看着,一直看到我消失在拐弯处,我每次出门,都要叫我把警服穿上,她为她的儿子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而深感骄傲,天好时,也会带我去串
个门,警服也必是要穿的。此番回来,人去楼空,房间里、厨房、卫生间、处处都是妈的身影在转,阴冷凄清的房屋里,满屋子装着对妈妈的怀恋与思念,打水时,窗前再也没了妈的慈影,我提着水瓶,转过弯,那小楼一出现在视线里我便觉得妈在那里一直看着我,告别那幢小楼时,再也看不见妈妈挥手喊:阿国再见了。尽管妈那时也是哭着喊的,但有总比没有强。我也含泪与妈挥别,心里总想着还有下一次呢,可命运只安排了一次!晚期的肺心病,把妈折磨得精疲力竭,妈很美的,一生都十分要漂亮、要强,可病中的妈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了,一脸的青紫,咳喘不止,我帮她洗脸擦背时,她都会舒心地说:“儿啊,娘好象脱了层壳似的,非常舒服,谢谢我儿了”。我听着默默地转身去抹泪,真有惭为人子的愧!妈病成这样,实在是需要个人服侍左右,子女不们都在西北上班,请个保姆总可以吧,可妈又是个犟性子,说什么也不让请,“花四、五百元请个保姆,我还是到敬老院的好了。”
我是2000年的春节去探望母亲的,腊月廿六妈给我过了个41岁的生日,装蜡烛戴寿帽,妈快乐得象个孩子,饭菜弄好了,妈点上蜡,让我许愿,我含泪看着烛光里的妈妈,脸浮肿着,极度的虚弱,却开心得不行,过年就我们母子俩,弟弟、妹妹、弟媳、妹夫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全家人都打电话过来拜年,妻也专门打了半个小时的长话。我背过脸去抹了泪,怕妈见了,我说许愿都是为自己能实现一桩特别想成,又成不了的事,人才会借助神力来帮助自己实现愿望,我许明愿,你是信天主的,我只希望能减轻妈的病痛,还我一个健康的妈妈。妈无奈地摇摇头笑笑,傻儿子,妈这病是没治了,美国总统、邓丽君那么有钱有名望的人,不照样治不好吗,说着妈的目光又暗淡下来,我真后悔,该说些别的,生命留给妈的快乐已经非常有限了!我吹了蜡,妈切蛋糕,一定要我给小康送些过去,小康又送来了些糯米糕、糯米团、一条大鱼。2000年的春节是妈渡过的最后一个值得高兴的春节,我的心里也轻松了一点点,妈这病关键是要养、保暖,心情还要好,只要能挺过冬至,就又能捱过一年去。
下次再见到妈时,已经到了诀别前的病榻上了。
十几年前就听到妈晚上在唱,有时问她,她总说在梦里不知道,她告诉我,其实她是知道的,那是病折磨得不能平躺,夜夜都得坐着睡,与其让孩子们听到妈在病痛中呻吟,还不如让你们只听到妈在唱山歌!我可怜的妈妈,晚年的日日夜夜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
2001年12月3日,接到了妈病重的消息,12月1日我出差去了农场,5日回到西宁,下岗在家的妹妹6日就赶到了宜兴,立即住院抢救,12月13日病情基本稳定了,我和弟弟远在千里之外,天天在长途电话中听妹妹汇报妈的病情,刚有了好转妈就要出院,妹妹和大夫不让出,她硬是出了院,妹妹又犟不过她,还把妹妹臭骂一顿,她是不愿意给儿女增添负担。可出院两天病情就恶化了,人也昏迷了,又二次住院抢救,16日我们接到了妹妹报病危的电话,从这一刻起我们兄弟就关注上了一个叫血氧含量的指数,它是垂危病人生命体征的一个重要指数,正常人在120左右,一般人到60就进入了呼吸衰竭,报病危时妈的血氧含量是75,17日一早我们兄弟赶乘西宁至西安,由西安转机去上海的航班,早上登机前血氧含量是68,中午在西安转机是65,晚上7点才到上海,朋友的车在机场外面等着我们,出了机场就赶往无锡肺科医院, 这时血氧含量到了55!妹妹在电话里哭着喊:大哥呀,你们快点啊!妈不行了!9点我们终于赶到了医院,一进门就听见妈在呻吟,我们进去她的神智还清楚,她说怎么走了这么久啊?母子又见面了,但这是生离死别啊!生命监护仪上的血氧含量指数只有45了,主治大夫说,因为她长期缺氧,又不进行正规治疗,练就了超出常人的耐受力!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知道你们兄弟正在往这里赶,她想见儿子的信念和心劲支撑着她坚持到了现在!
20日妈的自主呼吸快没有了,人已经进入深度昏迷状态,医生说他们已经尽力了,在我们的一再苦求下,医生又向我们提出了两条建议:一是上呼吸机,二是请“上海专家”来试试,但要先支付1200元出诊费。我们接受了医生的建议,付了出诊费。上呼吸机的时候,象是在上刑具,深度昏迷中的妈被憋醒了,说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:你们不能让我太难过啊!让我好好走吧!看着妈妈的痛苦样,大家都悲痛万分,一筹莫展,妹妹更是悲恸不已哭倒在妈的病榻边。我们建议医生去掉了呼吸机,继续吸氧。两小时后“上海专家”赶到了,他简单看了看妈的病情,这时的血氧含量指数只有32了,主治医生和“上海专家”把我们兄弟俩叫到医生办公室说:人救不活了,你们准备后事吧。并要我们在医嘱单上签署“同意放弃治疗”的意见。2001年12月21日凌晨3点20分,妈妈停止了呼吸,她平静地走了,走得干净利索,象她生前一样,不给别人找麻烦,享年62岁。第二天就是冬至…………
妈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,她热爱生活,一辈子爱整洁、要漂亮,生活特别讲究细节,善良贤惠,勤俭持家,吃苦耐劳,在高寒缺氧的青海高原,生活奋斗了30多年,含辛茹苦,相夫教子,养育了我们兄妹,终于积劳成疾,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虽然她只是个平凡普通的上海女人,但她也象许多为青海监狱系统,作出过贡献的家属们一样,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30多年,奉献给了青海高原。
妈转眼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,在这大地复苏,万物生长的季节里,对妈的思念也象长了翅膀似地在这春天里疯长,她是家的核心,是温暖,是身心疲惫的驿站。在妈身上我看到了女性常常表现得比男性更坚强、更执著,更具人格魅力。女性是伟大的,作为母亲的女性更伟大,她们孕育了生命,她们孕育了春天,世界也因她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丽。